深夜,因塔警局,某間類似拘留室的房間裏,衛燃比在自己家還自在的坐在桌子的一邊,一手拿着戳着一大塊牛肉的餐叉,另一隻手的指尖夾着一顆燃到一半的華子,笑眯眯的看着坐在桌子對面柳漢宰。
相比一口煙一口肉再來一口酒的衛燃,柳漢宰卻毫無食慾,他的所有注意力,全都放在了衛燃遞給他的手機上,顯示的那母子三人的合影上。
「她們在哪?」
許久之後,柳漢宰將手機還給衛燃,直勾勾的看着他用俄語問道。
「當地醫院」
衛燃將叉子上的那塊肉塞進嘴裏,仔細的嚼爛咽下去,這才繼續說道,「或許明天一早,他們會搭乘我們的運輸機飛往喀山,然後你的兒子會被送去喀山當地最好的醫院,接受進一步的治療。」
眼瞅着柳漢宰張嘴想說些什麼,衛燃不帶停頓的繼續說道,「又或許等你下次見到他的時候,他已經完成了心臟起搏器的植入手術。」
「為什麼要幫我?」柳漢宰皺着眉頭問道。
「邊吃邊聊怎麼樣?」衛燃指了指桌子上的食物。
聞言,柳漢宰伸手拿起一塊麵包狠狠咬了一口,接着又拿起餐叉,戳起一大塊牛肉塞進了嘴裏。
與此同時,衛燃也叼着煙,放下餐叉幫對方倒了滿滿一搪瓷缸子冰涼的啤酒。
「謝謝」
柳漢宰含糊不清的道了一聲謝,端起搪瓷缸子,咕嘟咕嘟的一口氣灌了大半下去。
重新幫對方倒滿了冰涼的啤酒,衛燃放下酒瓶子,慢悠悠的吸了口煙,這才回答了對方剛剛的提問,「幫你僅僅只是因為好奇,想聽聽你的故事,比如,你是不是脫...」
「不,我不是。」
柳漢宰不等衛燃說完便立刻予以了否認,但很快,他卻再次端起搪瓷缸子灌了一大口,隨後鬱郁的答道,「我...我是。」
「為了你的兒子思光?」衛燃追問的同時,將煙盒連同打火機推給了對方。
「對」
柳漢宰點點頭,顫抖着抽出一支華子點上,「他有先天心臟病,兒童醫院的醫生說他需要安裝心臟起搏器才能活下來,但是醫院根本沒有心臟起搏器,而且我們也沒有那麼多錢。」
「所以你們跑...」
「我是四年前通過正規途徑來俄羅斯務工的」
柳漢宰似乎生怕衛燃在這件事情上誤會,連綿解釋道,「在伐木場擔任伐木工,也在礦場擔任過焊工,或者在冬天負責看守設備,只要能賺錢,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做。」
「還是沒攢夠錢?」衛燃下意識的追問道。
「是來不及了」
柳漢宰艱難的低下了高傲的頭,「我出來務工之前,醫生就說思光需要儘快植入起搏器,否則他恐怕活不過13歲。」
「所以...」
「所以在出發之前,我就和我的妻子定好了計劃。」
柳漢宰或許太久沒有找人傾訴過,又或許太久沒有機會訴說這些煩悶,所以他僅僅只是一口氣喝光了杯子裏冰涼的啤酒,根本不等幫他倒酒的衛燃發問,便主動繼續說道,「我們約定,在我出去工作的第三年冬天,她就帶着我們的兒子和女兒偷渡來俄羅斯。」
「他們是怎麼來...」
話說到一半,衛燃在對方瞬間警惕的目光中歉意的笑了笑,「抱歉,我似乎問了一個不該問的問題。」
很是認真的盯着衛燃看了能有半分鐘,柳漢宰的眼神也終於再次緩和下來,狠狠的咬了一口麵包,一邊嚼着,一邊含糊不清的繼續說道,「在那年冬天之前,我努力學會了常用的俄語,又用之前工作攢下的一些錢,換來
了和另一個準備逃跑的人一起去礦場越冬看守設備的工作。
那份工作整個冬天都看不到第三個人,我趁着那個機會,接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,然後帶着他們從...帶着他們逃到了葉堡。」
「葉堡距離這裏可不算近」衛燃委婉的說道,生怕自己的好奇心再次引起對方的警惕。
「是啊」
柳漢宰嘆了口氣,「本來,按照我的計劃,我只要和我的妻子各自找幾份工作。大概只要一年,說不定就
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 首席御醫 挽救你的生命,即挽救你的政治生命。 機緣巧合之下,踏入了半官半醫的「御醫」之列。 在展現中醫強大魅力的同時,曾毅也實現着自己「上醫醫國」的理想,一步步直入青雲! 本書目前已經正式結冊出版
首席御醫 挽救你的生命,即挽救你的政治生命。 機緣巧合之下,踏入了半官半醫的「御醫」之列。 在展現中醫強大魅力的同時,曾毅也實現着自己「上醫醫國」的理想,一步步直入青雲! 本書目前已經正式結冊出版 都市兵王暫時無小說簡介
都市兵王暫時無小說簡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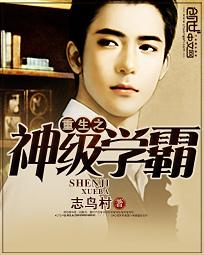 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
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