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方的兵力都不多,倉促廝殺,更沒法把人手糾合整齊。汲君立帶着追擊出外的精銳士卒,統共就只七八十人。這七八十人奮勇衝殺,緊盯着前頭逃跑的賊首。
便是那個似瘋狗也似咬去我臉上皮肉的小子!
就在汲君立眼皮底下,那可惡小兒狂奔亂走,時不時地污言穢語喝罵,與左右拈弓來射。夜間的野地里,人都看不清楚,弓矢飛過,颼颼聽個響罷了。汲君立全不畏懼,連聲大喊:「追上去!追上去!」
隨着他的指揮,數十甲士腳步匆匆,拉成了長蛇般隊伍,徑直離了故城店,往南面去。
南面數里處,就是滱河。乾涸的河道上碎石堆積,淺水淙淙趟過。地面不平,前頭逃跑之人的速度一下子慢了許多。
汲君立身邊有甲士高舉着火炬,火光映着前頭逃亡者跌跌撞撞的身形,忽明忽暗。能見到有幾個人被崎嶇地面絆住,狼狽不堪地倒地,然後手腳並用地繼續狂奔。
幾名弓手覷着機會,開弓便射。又有甲士急於殺敵,將身邊的短刀、手斧投擲出去。
箭矢和刀斧到處,前頭連聲慘叫。有個衣衫襤褸的老者,後腦被手斧劈中,登時倒地掙扎。而汲君立等人毫無顧忌地踏過他的身體繼續向前,連續四五人踏過以後,那老者的面門和半個身體都被壓進了河道里,水流淌過,帶起了血色。
眼前的情形,讓汲君立覺得非常熟悉。
他年輕時,在東平壽張縣為散巡檢下屬的小卒,整日裏與南面水澤間的盜匪搏殺。那時候,他也常如此刻,帶着數十人長途奔走,不分晝夜地追擊,將賊徒們一一斬殺,割了腦袋回去報功,換來酒肉,與同伴們分享。
那些賊徒們,本來都是和汲君立一樣的尋常百姓。多半因為朝廷括地而傾家蕩產,淪落為賊寇。但汲君立屠殺他們,殺得理所應當。在這世道,手中有刀便自橫行,哪有對錯,只有強弱而已。
汲君立願意追隨楊安兒,因為楊安兒是強者;楊安兒不得不向朝廷俯首,因為朝廷更強。而此時鐵瓦敢戰軍上下無不盼着起兵造反,也是因為朝廷的虛弱,越來越掩飾不住。
眼下既然要再度造反,總得幹得比前一次成功些。當日楊安兒在山東起兵,麾下少了經驗豐富的將士,面對朝廷派來的中都精銳,立即不敵。
這次可不是巧了?到了河北以後,左近遍佈着從漠南長城防線潰退下的散兵游勇。這些人個個剽悍,一旦糾集到己方旗下,必將極大增強成功的把握!
眼前這夥人,想來也是盤踞某地的潰兵,都是能廝殺的。一會兒抓住了為首那小子,必得取他性命,其他的人若願意投降,倒不是不可以。無非恩威並施,費些功夫。
「將軍,咱們離營寨有些遠了,還追嗎?」有部下問道。
另一人道:「須得小心埋伏。」
汲君立喘着氣,摸了摸臉。他臉上的傷口還在不停淌血,粘稠的血液已經順着脖頸流下來,在頸側的甲葉上凝成紫黑色的大塊。因為他身披重甲關係,一路奔走過來,滿頭汗水蒸騰,汗水浸過傷處,火辣辣地疼。
「左近潰兵全都是小股,誰來埋伏?眼前這股,說不定便是安肅州內有名頭有字號的人物了!抓住了這一夥兒,半個安肅州的潰兵都得降伏!」
汲君立連聲喝令繼續緊追。
但他畢竟是經驗豐富的武人,追了兩步,又道:「派兩隊人,沿着堤壩高處走!給我盯緊了左右情形!以防萬一!」
數人談話間,腳步難免慢些,眼看着被前頭的逃亡之人甩開了距離。
汲君立喊了幾句,扯動了臉上傷處,愈發疼痛。他的暴躁性子被激發起來,提刀在手猛追。
片刻間,眾人沿着滱河河道奔出三里多,北面的故城店,已經完全看不到了。
汲君立身邊着甲的將士無不氣喘如牛,腳步沉重;在河堤上頭沿途探查的同伴們被林地所阻,都甩在了後頭。
好在前方賊寇也快沒力氣了,跑得越來越慢。此前他們解救出來的一批故城店的俘虜,更是七歪八倒,好些人靠着別人的扶持,才能繼續前進。汲君立的部下連連張弓搭箭,又射翻了幾個。
天色暗沉,視野逐漸模糊。為了避開靠近河道中央的亂石,兩隊人都沿着河
第二十五章 夜襲(下) 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 最強狂兵 一代兵王含恨離開部隊,銷聲匿跡幾年後,逆天強者強勢回歸都市,再度掀起血雨腥風!簡單粗暴是我的行事藝術,不服就干是我的生活態度!看頂級狂少如何縱橫都市,書寫屬於他的天王傳奇!依舊極爽極熱血!(微
最強狂兵 一代兵王含恨離開部隊,銷聲匿跡幾年後,逆天強者強勢回歸都市,再度掀起血雨腥風!簡單粗暴是我的行事藝術,不服就干是我的生活態度!看頂級狂少如何縱橫都市,書寫屬於他的天王傳奇!依舊極爽極熱血!(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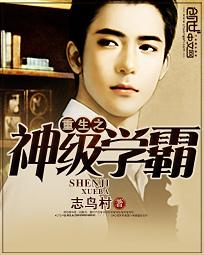 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
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 校園修真高手 【2014NextIdea原創文學大賞參賽作品】群號:199488169!期待您的加入!一個差等生,一次偶然的意外。讓他獲得了修真第一功法,從此命運徹底的改變。修煉異能,保護校花!用爆表的力量
校園修真高手 【2014NextIdea原創文學大賞參賽作品】群號:199488169!期待您的加入!一個差等生,一次偶然的意外。讓他獲得了修真第一功法,從此命運徹底的改變。修煉異能,保護校花!用爆表的力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