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着金菁那副神神秘秘的樣子,沈茶很嫌棄的撇撇嘴,放下手裏的公文,站起(身shēn),穿上斗篷就往外走。
從小一起長大,沈茶很清楚刻在金菁骨子裏面的那股惡趣味,別看表面上是個翩翩公子,整天笑眯眯的,其實是個(性性)格特別惡劣的傢伙。平時說話的時候,就喜歡說一半留一半,看到別人抓耳撓腮、絞盡腦汁猜他的真實想法的樣子,就特別的享受。如果碰上他極度興奮的時期,那就更不得了,如果盤算着說十句話,真正說出口的也只有一句而已,剩下的就要別人去猜,要不就讓別人求他說。
沈茶是懶得跟金菁玩這種你猜、我猜的把戲,也不知道是不是近期睡覺的時間太少,需要處理的公文、戰報太多,她整個人都昏昏沉沉的,需要出去吹吹風,徹底的清醒一下。
金菁一看沈茶出了大帳,趕緊放下手裏的點心,抓起自己的大氅也跟了出來,看到沈茶哪兒也沒去,就是站在大帳前面發呆,稍微鬆了口氣。
「這麼冷的天兒,跑出來做什麼?」金菁穿好自己的大氅,又給沈茶把兜帽戴好,「這麼多天都沒有好好休息,萬一着了涼、生了病,可不是鬧着玩的。」
「坐太久了,(身shēn)體都僵了,要稍微活動一下。」沈茶抬起頭看看碧藍的天空,輕輕嘆了口氣,「大帳里太暖和了,腦子都不好使了,清醒清醒。」她看看金菁,「小菁哥也稍微動一下,吃了那麼多的東西。」
「一塊糕就啃了一口,哪裏就多了。」金菁有些擔心,「你這幾天心事重重的,到底在想什麼?」
「雖然我們一直都知道,金國內部的矛盾很深,而且還是那種無法調和的,亂起來是早晚的事,但沒想到來得這麼快。按照我之前的預計,完顏萍怎麼也要找個藉口跟咱們或者遼打上幾次,暫時將那些反對她的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,抓緊時間建立自己的勢力。等到那些人回過神來,她已經強大起來了,再進行正面的決戰。可沒想到」她轉過頭看看金菁,「我覺得光憑為母報仇這一點,不足以讓她這麼快就對完顏宗承動手,完顏宗承這個時候昏迷,對她其實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,這裏面一定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原因。」
「天有不測風雲,人有旦夕禍福。她母親的那點事,大概還有外人知道,說不定是有人借着她的手,收拾了完顏宗承,順便也打了完顏萍一個措手不及。」
「一箭雙鵰嗎?」
「這是一種可能,但也不一定,我們也沒證據。」金菁呼了口氣,「或許事(情qíng)的真相沒有我們想的那麼複雜,完顏宗承的(身shēn)體就是不如從前,一下子就不行了,所以,給了完顏萍、完顏家其他人,還有那些虎視眈眈的部族一個機會,現在就看誰的拳頭硬了。」
「或許吧,但願是我想多了。」
「呵,你這幾天想的,恐怕不單單是這個吧?還瞎琢磨什麼了?都說出來。」
「這個確實不是我的重點,我現在倒不擔心他們會打得多慘烈,只是現在這種(情qíng)況,我們想要找尋當年的真相更困難了,是不是?」沈茶轉過頭,和金菁對視一眼,「當年的知(情qíng)人,順順利利活到現在的本來就不多了。經過這次戰亂,剩下來的就更少了,更嚴重一點,也許一個都不剩了。」
「有沒有那些人,對我們來說其實不重要,完全不用這麼擔心。」金菁拍拍沈茶的胳膊,「雖然很多案子裏面,證人是關鍵,但這種通敵的大案,物證是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那個。證人的口供是可以改的,物證更改的困難要大的多,是不是?」
「這麼說倒也是說得通的。」沈茶點點頭,「但是,當年的卷宗,我們都反反覆覆研究好多次了,卻沒有找到真正定罪的那個關鍵物證。人證的口供是含含糊糊的,所提交的物證,也是經不起推敲的。就連陛下也搞不明白,先皇當年到底是憑藉了什麼,那麼利索的處決了薛伯母。」
「誰說不是呢,就因為那個案子判的含含糊糊的,要什麼都沒有,人證也好、物證也好,完全構不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,我們才會覺得蹊蹺,才會花了這麼年的時間探尋真相。」金菁伸了一個懶腰,左右看看,確認沈昊林和薛瑞天沒有躲在哪裏偷聽,這才說道,「當初用來定罪的物證,絕大多數都是大王子和薛伯母
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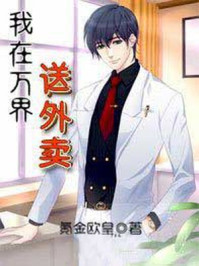 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
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 惡魔篇章 如果 你餘下的生命,只有幾個小時,你會做什麼? 是安靜的等待,度過最後的時光,還是放手一搏,為生存而耗盡最後一絲力氣? 行走在陰影之中,暗黑是最好的掩
惡魔篇章 如果 你餘下的生命,只有幾個小時,你會做什麼? 是安靜的等待,度過最後的時光,還是放手一搏,為生存而耗盡最後一絲力氣? 行走在陰影之中,暗黑是最好的掩 仙武世界大反派 BOSS之友! 主角公敵! 女主克星! 終極反派! 古霄在不同的世界中穿梭着,反派逆襲,踩死主角,俘獲女主芳心! VIP書友群:521621432,全訂的書友都可以加入進來,血月將在
仙武世界大反派 BOSS之友! 主角公敵! 女主克星! 終極反派! 古霄在不同的世界中穿梭着,反派逆襲,踩死主角,俘獲女主芳心! VIP書友群:521621432,全訂的書友都可以加入進來,血月將在